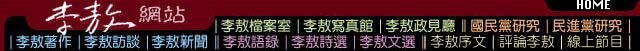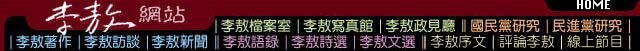文/楊瀾工作室 1999/07/15
七月十五日下午,台北在細雨中散發著潮熱。馬路兩邊,摩托車三三兩兩地淋在雨中。東豐街上各式台菜小館正打烊,幾個行人面無表情不緊不慢地撐傘走著。李敖的書房到了。
他比我想象的年輕得多。這位“中國當代最杰出的批評家”今年六十四歲,但看上去卻只有五十歲上下,一條紅色領帶更襯出他的活力。近年來他外出總穿一件紅色夾克,這種囂張的顏色和他極快的語速一下子把我從夏日午後的懶散氣氛中解放出來。
李敖是從不會讓你感到困的。他象一位嗅覺靈敏的獵人,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逃不過他的注意,同時他又像一只長期被追殺的野獸,隨時準備跳避陷阱,並侍時反撲。於是,接近他的人也在不知不覺中進入活躍狀態。
“您在回憶錄中說,因為常被出賣,所以對人就有了警備。凡來人必先假設是壞人,先小人後君子。請問我今天來採訪您,您會如何對待呢?”我的問題帶了點挑畔。“你一看就是好人。”他立刻回答,說得一屋子人都笑起來。
(一) 與人鬥其樂無窮
有一次,在接受台灣媒體採訪時,李敖曾說:“其實我這一生是失敗的。你們以為我說了那麼多,寫了這麼多,真有什麼作用嗎?”
他喜歡鮮艷的紅色,但有時候心裡面卻是灰色的。
不過,這些灰色情緒決不被允許主宰李敖的生活。六年的牢獄之災,幾十場的官司,96本書的被查禁絲毫不能改變他頑強好鬥的性格。
“這一點我象我爺爺。他在清未從山東闖關東,一生做過響馬,也打過響馬,是個極其凶悍的人。”李敖談起爺爺,就像是在談一位“鐵哥們兒。”
“你當年反蔣介石父子的專制,今天他們都已離世,你反什麼呢?”我問
“讓我給你講個笑話。我當兵時,經常要喊‘國父精神不死’的口號。一次軍官領口號說錯了,說成‘國父不死’。旁邊有人提醒說:‘還有精神’。於是軍官就忙改口:‘國父不死…還有精神。’蔣介石、蔣經國雖然死了,但李登輝還在。他剛接班時,我就講他有問題。
大家說怎麼可能呢,李登輝是台灣人,是教授,是基督徒,能有什麼問題?我就說:“你們別忘了他是蔣氏父子精挑細選出來的接班人。很快我就証明了──全世界我最早發現証據,說明李登輝是共產黨員的叛徒。”李敖越說越激動,目光逼人。提起李登輝前不久在接受德國記者採訪時提出“特殊國與國關系”,李敖的氣也不打一處來。“李登輝是個混蛋,按民間的話講就是蜢蚱鬥公雞,活得不耐煩了。”
李敖反台獨是盡人皆知的,可是歷史有時也會開玩笑。他從26歲起寫文章與國民黨做對,後者一直想找個“通共“的罪名把他抓起來,但苦於他太年輕,來台灣時才十四歲,無法被定性為“共匪”。
1972年他第一次被捕入獄,直接罪名是協助彭明敏偷渡出逃,於是被扣上“台獨”的帽子。過去,反國民黨專制的陣營統稱“黨外”,而後來隨著民進黨的產生,台獨勢力突出,李敖與之也就分道揚鑣了。
“如果台灣人自大狂妄到一定程度,就會產生痛苦。有人問我:‘你難道不是站在中華民國的土地上嗎?’我回答說:‘不,我是站在中國的土地上。”這段話是今年五月,他在“李敖禍台五十年”的講演會上說的。當天,原本只能容納三千人的禮堂里擠進了六千人。
看來,李敖的鬥爭還遠遠未到偃旗息鼓的時候。而這位相信與人鬥其樂無窮的作家也用不斷的進攻給自己的思想之火添柴。至今,他已寫下了近三千萬字的作品,不過,他自認為“立德”比“立言”做得更出色。
“台灣太小,中國的一個省而已,無功可立。我比別人“立言”都多,但我覺得自己的本事是立德。在台灣,我是真正做了一個走過從前,始終如一的人。我一個單干戶,個體戶,公開站出來跟國民黨干,雖然坐牢,雖然受刑,可是至今沒有改變。我覺得這個是一般人做不到的。”
(二)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就骨氣和傲氣來說,你還真不得不佩服李敖,他說的話雖然是自夸,卻都是事實。讀他的回憶錄時,我對其中一段獄中生活的描述印象深刻。那時牢房里只有在中午才會射進豆腐塊般大小的陽光。為了捕捉到這珍貴的陽光,李敖就依次把左臂、右臂,然後是頭、頸伸進光區去晒一晒,以保証自己的健康,準備出獄後繼續鬥爭。“難道你沒有自我懷疑的時候嗎?”我問。“有。當我被行囚時,審問我的人就把幾支圓珠筆夾在我左手手指當中,然後抓住我的右手,放在左手上,再從外面捏我的右手,這叫“斬指”。你看《儒林外史》,里面女孩子受類似的刑罰是受不了的。當時他們放開我的手以後,還跟我戲謔性地開玩笑,說 '李先生,不要怪我們,不是我們讓你疼,而是你的右手讓左手疼。我當時疼得要死,也要開玩笑說, '我也不怪自己的右手,我怪圓珠筆。其實那時我怪自己,我有一點難過,自問為什麼你闖了禍,要受這皮肉之苦。你的肉體背叛了你的精神。精神還是穩定的,但肉體開始痛苦。所以我才知道人的成長不是一開始就很英雄豪杰的。聖女貞德也是寫了悔過書的。經過那個動搖的過程才堅強起來。而且越來越凶。果不其
然,李敖出獄後沒幾天就召開記者招待會,宣稱“天下沒有白坐的黑牢”。以往整治過他的法官被他口誅筆伐,死纏硬打。一時“官不聊生”。即使打不贏官司,也要讓對手筋疲力盡。我笑著問李敖“你這不是刁民嗎?”他氣都不喘地應聲答到:“對,我就是刁民,可我站在正義一邊。”“為什麼不能原諒一些跟你有個人恩怨的人呢?”“可以原諒,先打倒,後原諒。就像清朝彭玉麟所說的,'烈士肝腸名士膽,殺人手段救人心',雖然表現出來是金剛怒目,可骨子里是菩薩低眉。你要注意那種有仇不報的人,就是忘恩負義的人。因為他感情太淺,有仇不報,有恩就會忘。中國人總說 算了',可是猶太人就要以牙還牙,以眼還眼。我們應該學猶太人。”對於李敖的凶悍和偏激,不少人是看不順眼的,甚至一位香港著名作家就曾對我說:“我愛極了李敖的文章,也總有人要引荐我們認識,我卻拒絕了,因為金庸曾經跟李敖談了一次話,意見與他有不合之處,就被他寫了文章罵得好慘,有了前車之鑒,我還是敬而遠之吧。”據稱,能與李敖長期做朋友的人不多,一旦有了齬齟,李敖有本事把陳年爛谷子都掀個底朝天,公開讓你下不來台。偏偏這家伙記性還特別好,什麼書信、錄音也統統留著。聽了這些話,你總會覺得李敖不夠厚道。不過,李敖成
其為李敖的原因就在這里。誰能在華人社會中找出第二個李敖來呢?倒是讀者們自有公論。有人說:“有時候我們愛他愛得要死,有時候又討厭他討厭得要死,但他的魅力無法抗拒。”又有人說“台灣社會如果沒有了李敖,將多麼寂寞!” 更多的人認為“李敖說出我們想說而不敢說的話,他的話雖然可能很偏激,但就像是晨鐘著鼓,當頭棒喝。讓人清醒。”其實,把李敖的“惡鬥”只理解為個人恩怨是不夠全面的。97年他義助慰安婦的舉動就廣受贊賞。二戰期間,日本逼迫朝鮮、菲律賓中國大陸及台灣的女子做隨軍妓女,美其名曰“慰安婦”。這些女子最多一天要“接客”六十余次,慘不堪言。戰後,日本政府從未正式向受侵略國家道歉,而只用一個民間組織找到一些慰安婦,私下里給她們每人兩萬美金,讓她們簽字和解。台灣至今有當年慰安婦五十幾位,這些生活悲慘的老婆婆想要這筆錢,但是國家民族大義又告訴她們不能要日本人這個窩囊錢,李敖知道後,站出來說:“你天天引得這些老太太天人交戰是不合乎人情的。”他想起北洋時代,曹錕賄選。張作霖反對曹錕,就對那些議員說:“曹錕給你們多少錢,我也給你們多少,只是不要選他。”由此,李敖突發奇想,拿出自己所有的藝朮收藏品義賣,所得三千三百萬新台幣(合一百多萬美元)分給這些婦女。讓她們理直氣壯地去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這是李敖近年做的最痛快的一件事,不過畢生收藏化為烏有,每每想起,還在心疼。我看到沙發邊上有一只青花瓷缸,古朴雅致,就安慰他說:“總算留下了一件。”李敖兩手一攤,說:“可惜,這是個仿制品,不值錢的。”
(三)欣賞謔感,向往悲愴總聽人把李敖與魯迅相比,因為他們文筆的犀利、刻薄頗具相象之處,又都以“痛打落水狗”的批評家姿態出現。但李敖並不同意這種看法。“我認為這樣的類比是不太正確的。我從來不‘橫眉冷對’,我是笑嘻嘻的,可能算個笑面虎吧。如果我沒有這種頑童性格,恐怕早得了胃癌,慪氣慪死了。我喜歡魯迅的《阿Q正傳》和《中國小說史略》,但魯迅用的是日本文法,有時候文字讀起來別扭。而且他的情緒化語言很多,資料不足,我的文章表面上看起來很情緒化,其實把這層辣椒拿掉之後,下面有肉,有資
料。我認為魯迅是被過分炒作了的。”說到“我是笑面虎”時,李敖一臉童真,得意得很。中國文化一般都比較正統端庄,沒有太多“謔感”。李敖飽讀詩書,卻是個例外。這方面他特別欣賞十八世紀法國思想家伏爾泰。伏爾泰被放逐英國多年,他找到當地發行彩票的疏漏,大賺一筆。流放期間,他的著作被源源不斷流傳回法國。八十歲時,他終於獲準回到祖國。海關官員問他:“有沒有帶什麼違禁品?”他頑皮地回答說:“只有我本人是違禁的。”伏爾泰死時把棺材的一半埋在教堂里,一半埋在教堂外,臨終也不忘開個玩笑:如果真有天堂,我就上天堂,如果要下地獄,我還可以從另一端逃走。李敖著實羨慕這位二百多年前的法國老哥的運氣。
李敖的專業是研究歷史,於是我問了他這樣一個問題:“日本作家池田大作曾拜訪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問他:‘假如可以選擇,你最希望做哪個時代,哪個地方的人?’湯恩比回答:‘我最希望做唐朝絲綢之路上新疆那地方的人。’李敖先生會怎麼選擇呢?”“我也想生在唐朝。因為那時的人有一種氣概。記得徐敬業的好朋友單雄信與唐太宗作對,唐太宗要殺單雄信。徐敬業到皇帝那兒求情,說寧愿自己降級也要保全朋友的性命。唐太宗不允。徐敬業就割了自己身上的一塊肉給單雄信吃了,意思是:我雖無法救你,但我的一部分隨你去了。”李敖停了一會兒又加上一句:“現在全世界都沒有這樣俠義的人了。”這份對“義”的向往倒充滿了中國味,它讓我想起李敖寫的唯一一部長篇小說《北京法源寺》。這部寫戊戌變法的小說特別著墨於譚嗣同決定去留生死的選擇。譚嗣同認為中國變革不成功是因為沒有人流血,於是懷著“自吾始”的心態慷慨就死。如果這件事發生在李敖身上……?“不,我決不做譚嗣同,我做梁啟超。”
“把容易的死讓給別人,把艱難的活留給自己?”我想起了《趙氏孤兒》里的情節,於是這樣問。
“對。你看後來梁啟超辦《新民叢報》,能發揮那麼大的力量,把清政府推翻。他不要做烈士,他要做成功的人,做烈士的人是笨的。”
“可是如果當年人家把你抓起來殺了,你不也成烈士了嗎?”
“可是我當時的罪名是判不了死罪的。我看死他們不能殺我。”李敖用手勢加重自己的語氣。“我認為做一個成功的人比做烈士更正確。”
(四)女人堆里是非多
別看李敖在男人世界裡橫沖直撞,耀武揚威,女人堆裡他可是麻煩多多。二十歲時,正上大學的李敖愛上了一位叫“ 君若”的女生。但女方家嫌他太窮,強迫女兒中止與他的關系,並揚言:“如果你以後做了總統,我們也不高攀,如果做了乞丐,到了我家門口也請多走一步。”李敖為此自殺,未遂。
二十七歲時,他與王尚勤同居。王後來在美國生下一女。如今這位女兒已三十有六,在美國結婚,喜歡住高級住宅,開豪華汽車,此住、行兩項全由李敖提供。
“為什麼?因為你有歉疚?”
“是的。因為她是我的私生女。又因為該給她教育時,我在坐牢。”後來李敖還有過幾位女友,因為他入獄而生分了。
“在我喜新厭舊之前,女人就把我甩了。”李敖自嘲道。四十五歲那年,李敖有了一件轟動台灣的婚事。電影明星胡茵夢與他閃電結婚,又在三個多月之後閃電離婚,並在一場官司中作証,說李敖“侵占他人財產”,李敖因此再度入獄。五十歲時,法院給李敖平反。兩人的筆墨仗打了十八年,仍在繼續。我在台北的書店里到處可以看到胡新出的自傳,譴責李敖當年敗壞她的名譽,而李敖則在自己的晚間電視清談節目中不遺余力地証明前妻迷信,記憶力不好,和“不義滅親”。
“曾經相愛的人如今惡語相向,不可悲嗎?”我忍不住問。
“可悲,但我們所談的部分不止是男女私情,而更關乎世道人心 我看不起,但還是要計較。”
另一位給李敖帶來麻煩的女人是他的親生母親。
“八位子女當中,只有我愿意和她住在一起,贍養她,但她卻總說其他七個是孝子,只有我不好。給她派個佣人,她說是來監視她的。我入獄時,有一處房產寄在她的名下。她沒有經我同意就拿去做抵押,給我弟弟做生意。結果國民黨沒有把我的財產沒收,倒是我媽媽替我沒收了。”
“不過,”李敖苦笑著說,“母親和女兒帶來的苦惱是 有時候說不出口的,象我這種心狠手辣的人,對她們下不了手。有什麼辦法呢?”好在李敖現在的小家庭生活還算美滿。妻子是他十五年前在馬路上認識的。當時她正在一邊喝易拉罐咖啡,一邊等公車。李敖覺得她很漂亮,就上前搭訕。見我露出驚奇之色,李敖理直氣壯地解釋:“別人會說,為什麼不找人介紹呢?但是沒等找到介紹的人,她就要坐公車走了。別人還會說,如果被拒絕了不是很沒面子嗎?可見他們重視自己的面子過於喜歡女人。我不是這種人,遇到漂亮女人,我
要給她們一個機會。”現在兩人已有一個小女兒。李敖深知自己仇人太多,從不讓妻子、女兒見媒體。我發現在他書房中,各處都有裸女的照片,他的妻子倒也不介意。李敖說:“這些照片是我不同時期最喜歡的。敢把它們擺在外頭,說明我心里沒鬼,太太自然放心。”
而我們的鏡頭,為青少年觀眾起見,也就自然要避開它們了。李敖目前正準備用三年左右的時間編一本《句典》,精選中文里最好的句子,設立典范。而其中自然少不了他本人的好句子。他公然宣稱: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白話文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讓多少人氣得牙根發痒。李敖的傲氣和才氣讓人恨不得,愛不得,這讓我想起關漢卿寫的一首元曲《一枝花?不服老》,其中有這麼幾句:“是一顆蒸不爛,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響噹噹一粒銅豌豆。”
李敖本人也覺得這幾句用來描述他的性格算得貼切,而他更喜歡用這樣的話做個總結:“如果有來世的話,如果我不是李敖,我愿做李敖第二。”窗外,雨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