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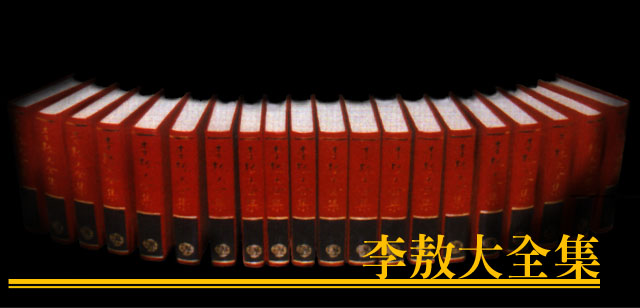
「世論新語」在書名上,自是從一千五百年前劉義慶「世說新語」而來。中國人寫書,普遍毛病是犯頭巾氣,「世說新語」卻是脫帽後的閒談,每個故事落墨不多,或優美、或灑脫、或驚心、或動魄,都是很有味道的。 老友段宏俊辦「世界論壇報」,拉我寫「世論新語」專欄,雖在文體上、範圍上,不同於一千五百年前的著作,但在落墨不多、為文恣肆上,卻媲美前人。我曾自負性的寫實說「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心裏都為我供了牌位」,設想我如果寫的不是白話文而是文言文,則早生一千五百年,其前三名,也非我莫屬。劉義慶後五百年出了歐陽修、蘇東坡,千百年後重看他們的文章,卻發現他們文勝於質,文字優美、思想貧乏。我想我若生在古代而以文顯,縱筆所之,亦必於文言文上有以開拓新境界。 我這些話,並非狂言。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在比較務實的清朝文章家眼中,賈在漏洞百出。清朝的方苞少有文名,並以此自矜,後來到了北京,見到萬斯同,萬斯同跟他說 :你整天迷戀古文,其實唐宋八大家中,除了韓愈文章中稍通聖賢之道外,其餘七家,作了一輩子的文章,所說多空洞無裨實際。方苞經這一點醒,政治經學,以「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自期。他是桐城派開山祖師,桐城派作文標榜「義法」。「義」是「言有物」,「法」是「言有序」,立意固佳,可是他們的才具卻跟不上。他們在義上雖然不像宋朝人明朝人那樣空疏無學,但在思想上還是難脫中國道統乃至宋明理學的樊籠,則其「義」也,也就無足觀;至於「法」上,更是放不開,從佛經的禪語、到語錄的口語;從駢文的徘語、到詩歌的集語。…… 在在都是他們嚴防之列。結果文章選出來、寫出來,謹嚴有餘、變化不足;規格林立、雄奇獨缺。論思想,不能超邁古人;論文字,且在古人之下。桐城派在作文上下了那麼大的功夫,結果空忙了一場,更使中文頭巾氣了。中文的最後解放,在文言文方面是由梁啟超總其成的。梁啟超自謂:「風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鍊。至是(辦「新民叢報」)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梁啟超雖然把文言文寫活了,但文言文究竟是一種死文字,再活也是「炸屍」「趕屍」式的活法。到了文學革命出來,終由白話文代領風騷,自此中文正宗,自文言轉為白話。白話文當行,大家都寫白話文了。 白話文看起來雖是口語易寫,但在文字上,由於正宗基礎太薄弱,真正能寫得好一手白話文的,並不多見,反倒是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舊的嗎了呢派」、「新鴛鴦蝴蝶派」等錯路上去,再加上思想上的混亂與無知,所以論文字、論思想,殊多敗績。這種敗績,直到李敖出現,才一切改觀。 這本「世論新語」,是一種「短促突擊」式文體的結集。我生平善寫各體文章,但一連串寫了這麼多「截長補短」的專欄,卻是縱橫文海許多年來的第一次。愛其出神入化、樂其新奇可喜,特彙而成書,以給讀者在看「千秋評論」以外,別得異趣也。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