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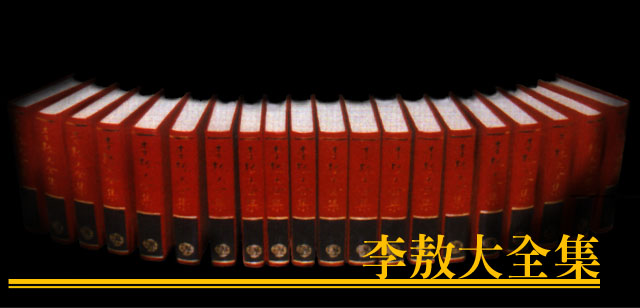
——從「中國名著精華全集」談怎樣讀書 (代序)
■你李敖讀書讀得最多,真是中國第一嗎? □最近香港報上說:「李敖很可能是五十歲以下的當代中國人之中,讀書最多而又最有文采的人。」前年童軒蓀信上說:「去年炎夏,居浩然自波士敦西來,在敝寓住了五天,這五天裡上下古今談了一番,他卻特別推崇你老兄,說是『念書太多,我們不可及』。」……這些話,都非過譽,在讀書方面,我讀書之多,的確可說中國人無出其右。 ■當代中國人以外的中國人,就是所謂古代中國人,總有比你讀書讀得多的吧? □古代中國人讀書讀得最多的無可考,唐朝詩人杜甫說他「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其實古書字大,萬卷書並沒有多少。清朝陳夢雷說他「讀書五十載」、「涉獵萬餘卷」,由他編出的「古今圖書集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四冊)看來,陳夢雷讀書之多,該在古人中考第一。陳夢雷是清朝進士,他的淵博,被皇家王爺看中,叫他編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古今圖書集成」是根據中國一萬五千多卷經史子集的典籍編成的,前後用掉了四年半的時間(一七0一——一七0六)。全書共有一萬卷、六彙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七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冊,一億四千四百萬字,分裝五百七十六函。這部大書,「凡在六合之內,巨細畢舉,其在十三經、二十一史者,隻字不遺;其在稗史集者,亦只刪一二。」它的體大思精,確屬空前。陳夢雷可說是苦命的人,三藩之亂時,正趕上他回家探親,被靖南王耿精忠脅迫造反,不幹就殺他爸爸,他沒辦法,只好合作,不料造反失敗,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賣——不肯證明他的清白;又被張冠李戴,誤會成「行賊偽命」的陳昉,所以罪上加罪,被發配到東北做奴隸。過了十六年後,趕上康熙皇帝東巡,把他召回來,叫他陪皇帝的第三個兒子誠親王讀書,在這段優遊的歲月裡,他「目營手檢,無間晨夕」,終於編出了這部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康熙皇帝死後,苦命的陳夢雷又開始苦命了。他所依靠的皇三子誠親王失勢,繼位的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對哥哥的親信們大加整肅,陳夢雷則首當其衝,又被「發遣邊外」,送到了東北。這時陳夢雷已經七十多歲了,他死在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活了八十多歲。由以上杜甫和陳夢雷都讀萬卷書的標準看,杜甫的讀書成績就不如陳夢雷,因為陳夢雷把他的讀書成績用編了大書做為嘉惠別人的展示,可是杜甫就沒有這種效果了。
披沙揀金的好處 ■你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是不是有上承陳夢雷這種心願呢? □還不止此。在十二世紀,一個偉大的中國有心人鄭樵,在隱居山林、謝絕人事的專事寫作裡,曾立下「集天下之書為一書」的雄心大願,但他五十九歲死去,沒有完成。如今,八百年過去了,這種雄心大願,有賴於新時代的有心人和新時代的出版形態來完成了。新時代的有心人要做「集」舊中國「天下之書為一書」的新嘗試。它的形態所決定的方向,必然是劃時代的方向。 ■這個方向的指標,就是「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嗎? □就是。它的完成,該歸功於遠流出版社的王榮文。王榮文是中國出版史上最有創造性大手筆的小兄弟。五年前,他和我合作,出版「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創造出中國出版史上劃時代的大轟動。四年以後,他寫信給我,說:「香港那邊,臺灣這邊,都整理了無數的國學材料,但幾乎還沒有一個人為現代讀者整理出一套可以讀得下去、讀得懂、包含各方面文化精華的中國名著全集。」因此他相信:「如果能把中國的東西整理出一個定品」,該是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這件事,就是出版「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王榮文把這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逼我來做,要我來「表現這幾十年來海內外研究中國成績的總和」,我相信他把人找對了。我的確是主持這一工作的最佳人選。記得十九年前,我與徐復觀對簿公堂,兩人一邊打官司一邊喝咖啡,談得非常開心。徐復觀心血來潮,說了一段真心話,他說:「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書,念得比我們還多還好,你卻主張全盤西化!如果你來宣傳中國文化,你宣傳的成績一定比我們都好!」徐復觀說得沒有錯,我真是對中國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會看古書,會利用古書、活用古書,古書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為神奇,看古書對現代人沒什麼用處。不幸的是,據我所知,看古書的人,很少不陷入泥淖的,一百個有九十九個,都變成搖頭擺尾的老夫子,思想迂腐而泥古,愈來愈混蛋(年輕時小混蛋,年老後老混蛋),因此我倒了胃口,從不鼓勵人看古書了。但是,如果有好的選本,再有「讀書得間」的訓練,古書中畢竟還有一點披沙揀金的好處,可以給我們活用,問題是誰來主持這一化腐朽為神奇的工作呢?王榮文看出來非李敖不可,李敖也看出來非李敖不可,於是,工作便這麼敲定了:王榮文找對了人,李敖找對了書,徐復觀的一個好夢,居然在十九年後,在我無改全盤西化的大前提下,居然成真了。
「讀書得間」的重要 ■我們相信你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中提供了「好的選本」,但是,你所說「再有『讀書得間』的訓練」,又怎麼提供呢?古話說「鴛鴦繡取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你可不可以多說一點始末,把「金針」「度」給大家呢? □「讀書得間」是在讀書時能夠讀出書中的「竅」、領會出字裡行間的學問來。英文中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就正是此意。讀書要有這種本領,讀古書更要有這種本領。硬讀古書不行的。許多用功的人,終身「白首窮經」,可是因為方法不得當,結果只變成「有腳書櫥」。最後事倍功半還算是好的,因為他們經常徒勞無功。很多人讀了一輩子書,結果變成老學究,就是一個證明。所謂古書不能不講求方法的硬讀,因為古書中,有許多只是書生理想,並非社會現象,書生在那兒託古改制,你在這邊信以為真,你就上當了。又有的古書中,只是道德法律,也非社會事實,古代的社會事實既有距離,現代的你卻盲目相信,你又上當了。所以讀古書,首先要「辨偽」,辨偽以後,就要區分出來什麼書是書生理想、什麼書是道德法律、什麼書是社會事實。把這些分辨開,再融會貫通、互相印證,才算「讀書得間」。「讀書得間」以後,從而著述,才算「為往聖繼絕學」。否則的話,只是堆砌材料、暴殄文字而已。 ■「讀書得間」是不是就是要把書讀活?把死書讀活?這種讀活,多讀書是否會有幫助? □不一定。中國的知識分子讀書多的卻也不少,但是愈讀愈混蛋的,卻愈來愈多,這都是因為讀死書的緣故。很多人的基礎,根本是「呆子」,後來念了幾十年的書,變成了「書呆子」,辛苦半生,如此而已。我從前有位老師叫姚從吾,是遼金元史專家,非常用功,最後死在書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書,就好像一隻狗熊進到玉米園裡,折一根玉米夾在腋窩下,左摘右丟,弄了一夜,出園時還只是腋窩下那一根。——他們看過的東西隨時扔掉了!所以讀書無法使他們頭腦變好,反倒變壞。 ■這樣說來,這種人似乎選錯了行? □選錯了行。 ■可是他們也有著作呢,怎麼辦? □「隋唐嘉話」裡有這樣一段:「梁常侍徐陵之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今傳之江左。陵遂濟江而沈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為魏公藏拙。』」為了避免這種人「堆砌材料、暴殄文字」,他們的著作,實在該適度予以水葬才好!
一般讀書情況 ■古今中國人中,一般讀書情況是怎樣的? □大致可分兩派:一派是老學究村夫子派。他們白首窮經,一輩子讀了一些古書,可是他們的方法訓練太差了,又無法接觸到現代新學問,所以用新知治舊學的一套,他們一竅不通。他們雖然一輩子嗜讀古書、勤讀古書,但可笑的是,他們卻讀不懂古書,無法分析古書,也無法綜合出結論和真相。另一派是疑古派。他們是新一代的學者,不但博覽群書,並且會「讀書得間」,處處發現古書可疑、古事可疑。他們的典範作品是編輯「古史辨」和「辨偽叢刊」等,對古書的解釋,他們的功勞很大,成績也頗可觀。但是疑古派也難免有著兩大缺點:第一是疑古過度,往往犯了以書就我的毛病,大膽假設有餘,小心求證卻往往不足;第二是不太能用現代新學問(如天文學、原始社會學)做鑰匙,側面印證古書可信的部分,以致犯了全面抹殺古書的毛病。他們常說這本古書是假造的、那個古人無其人等等,其實不然。 ■請舉一個例。 □以「周禮」(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三冊)為例:「周禮」原稱「周官」,是漢朝劉歆改名「周禮」的。傳說是周公創立的理想政制,所謂「周公致太平之跡也」。因為它是中國政制書中最細密的一本,所以被視為珍寶。「周禮」將官職分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職)、夏官(軍事)、秋官(司法)、冬官(器物製作)六類。列舉每個官職的名稱、職制、人數和職務內容。從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顯然是後代的政治理想,寄託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發揮的。「史記」封禪書中雖然提到過「周禮」,但「周禮」的出現,卻在西漢末年,又因為它的制度與諸經不合,所以被人懷疑是劉歆偽造的,是偽造獻給王莽,以利於王莽的改制的。但是,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來檢查「周禮」,發現倒頗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後人可以憑空偽造出來的。因此,「周禮」從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的價值。因為「周禮」是四萬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制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說,宋朝王安石變法,便是一例。「周禮」是中國政制的烏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視。疑古派以劉歆偽造「周禮」而把「周禮」一筆抹殺,我就不相信劉歆可以偽造出用現代新學問可以印證出來的古代現象。
疑古派的穿幫 ■疑古派的大膽假設,死無對證,總可自成一說吧? □不然,死可有對證呢!以「孫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二冊)為例,就可證明了。孫武(前六—五世紀)是春秋時代吳王闔廬的客卿,是兩千五百年前的軍事家,他的著作「孫子」共有十三篇,後來發生了混亂,杜牧說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事實上,「孫子」只有五千九百一十三個字,這就是高誘所說的「兵法五千言」,高誘在曹操之前,可見曹操刪書之說,是不對的。因為「孫子」發生了混亂,孫武也就在疑古派眼中,出了問題,他的身世,遭到懷疑。其中最主要的有兩種:第一種是懷疑根本沒有這個人;第二種是懷疑他和戰國時代的孫臏為一個人。像錢穆就是靠後一種說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的古墓裡,出土了古代兵書,內有「孫子」,證明了這種懷疑,都是站不住的。出土的古書竹簡中,有漢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曆譜,可以斷定這批竹簡是兩千一百年前就已流傳的文獻;又由於竹簡中用字不避漢朝皇帝的諱,又可以斷定竹簡的古書,都早於漢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戰國,不過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統一思想,沒人有閒工夫造假書,所以竹簡中的古書,都是戰國以前的原裝貨,應無疑義。所以「孫子」確有其人其書,已是鐵證,只是古本今本有異文耳!古代流傳的「孫子」書——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孫子」書——即竹簡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處不同的,也多是虛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孫武傳」六篇,可補今本「孫子」的不足。古書死有對證,竟有趣如此!以這一死有對證的另一當事人孫臏為例,更可再對照一下:孫臏(約前三八0—約前三二0)的身世,在「史記」裡說得很明白。「史記」說:「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世傳其『兵法』。」這明明是說孫武有孫武的「兵法」,孫臏有孫臏的「兵法」。但是後來孫臏的「兵法」失傳了,由曹操在注「孫子」時,已經隻字不提孫臏的情形看,可能在漢朝末年,孫臏的「兵法」就已見不到了。就因為如此,所以後人就附會起來了,認為孫臏即孫武這個人、孫臏「兵法」即「孫子」這部書,一切都二合一起來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二號漢墓出土,竹簡中赫然有「孫子」,也赫然有孫臏「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二冊)疑古派這種笑話,在「尉繚子」上,又有了外一章。尉繚(前四世紀)的「尉繚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但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二號漢墓出土竹簡中,有古書「尉繚子」。「尉繚子」一直被許多大牌學者如錢穆等人懷疑是後代假造的書、是偽書,並且說得頭頭是道。但是這批竹簡一出土,證明了真金不怕眾口鑠,大牌學者也者,不過大言欺人而已(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二冊)。以上所說,無非是說老學究村夫子派固然不會讀書,疑古派雖然比老學究村夫子派高明,也難免被死有對證一番。——這大概是古人死不瞑目,因而如王安石所說的「死屍能報仇」了。
俞樾「土法煉鋼」 ■這樣說來,古今中國人中,一般讀書情況是不怎麼高明了? □大體上說,實在不敢恭維。當然有些個人是不乏會讀古書的,像俞樾,就是最突出的一位。俞樾是清朝進士,咸豐年間因為「命題割裂」,被革職為民;又因為「故里無家」,就在江蘇蘇州住下,後來到各地講學三十年。他「生平專意著述」。每一年下來,都「有寫定之書,刊行於世」,中國像他這樣勤勉而每年有成績出來的作者,實在少見。他活了八十六歲,全部著作收入「春在堂全集」(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六冊)。俞樾的名著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古書疑義舉例」出得最晚,寫得也最爐火純青。這書共七卷,把古書疑義分類寫成八十八條,用前無古人的科學方法,使人們知道如何認識古書。劉師培說這書「發古今未有之奇」,可謂定評。這書後來引得劉師培、楊樹達、馬敘倫、姚維銳等的仿作補作,影響極為深遠,俞樾雖然能夠「讀書得間」,但是,他因為沒有現代新學問的光照,全部的努力,仍是支離的「土法煉鋼」的成績而已。這一教訓,清楚的告訴了我們,沒有現代新學問的光照,讀古書也有瓶頸的。此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傳統下來的書的結構與素材,都有嚴重的問題。
工具書與方法學 ■結構方面,好像都是擠成一團,頭緒很亂、很難讀,是不是有工具書就好一點? □工具書是任何知識分子所必備的書。像辭典、年表、年鑑、百科全書、手冊、索引,以及一些必備的「非書資料」(non-book materials)等。在研究和閱讀上,雖然有所謂「個人需要」(individual needs)的不同,但就運用工具書一點上,卻沒有各行各業的分別。所以工具書在所有書中,應該列為第一優先。選擇工具書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容易找到」(easy to find)你所需要的答案;一個是「容易了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 to find what you find)答案。不合於這兩個標準的工具書,都不算是好的工具書。儘管它很有名,可是它卻使你頭痛。若舉一例:「康熙字典」便是,這書實在犯了難找的毛病。(但這種毛病,發生在笨頭笨腦的古人身上,猶可說也;發生在現代人身上,就太不可說了。你看看張其昀監修,林尹、高明主編的「中文大辭典」,你會驚訝的發現,這部以抄襲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為骨架的書,竟也發生「康熙字典」式的毛病,你說這些老骨董多笨!)辭典以外,工具書中的「年表」一類,縱貫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給人清楚的頭腦和時間的觀念。中國舊式的編年一類書,因為採取甲子干支紀日,時序檢核,十分麻煩。又以曆數屢變,常常需要推算,可謂不科學已極,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國傳統留下來的工具書都不合用。總之,從工具書上去讀書,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讀書得間」,工具書不夠。現代新學問反倒是最重要的。我以「儀禮」(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四冊)為例。儒家提倡禮治,關於禮的典籍,流傳了三種「經」和一大堆「記」,三種經是「儀禮」、「周禮」和「禮古經」。其中「禮古經」失傳了。「儀禮」和「周禮」傳說是周公作的,實際是戰國人的作品。「儀禮」是宗教儀式、政治儀式的總集,今本包括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服、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禮。這些都是古代禮的節目單。古代的貴族們一舉一動都有一套規矩,這些規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華,使當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於是就請專家們來幫忙,這種幫忙,叫做「相禮」(輔導別人行禮);這種專家,就叫儒。相禮相得多了,就累積出節目單來,到時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這種節目單的總集,就是「儀禮」。節目單最多的時候,多達五十六篇,後來丟了三十九篇,只剩十七篇,就是流傳到今天的「儀禮」。「儀禮」是十三經之一,歷來把它神秘兮兮的捧著,其實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來看,毫無神秘可言,只是很好的史料而已。只因它列名於經典之中,而經典早已在歷代中國人的意識裡,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位,大家不敢深究,並且限於治學方法,也無法深究。從而對古人的觀點與真相,簡直無法了解,眾說紛紛,其實只是附會或猜謎而已。由於近代方法學的進步,用這些間架,移做整理古書,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說經也好、解經也罷,種種無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學迎刃而解。
分類與走運 ■這樣看來,中國傳統下來的書,它的本來面目好像都給做了手腳了,讀這些書,還得先來一番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功夫才行? □對了。中國傳統中的一團雲霧,先在圖書分類上,你就先思過半矣。中國書的分類,最流行的,是四部(經、史、子、集)分類。四部分類從東晉以後通吃,變成了典型的圖書分類規範。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這種分類是相當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經部」為例,「經部」的一部分,近於百科全書式的總集,應分入總類、文學類、歷史類,其他部分(像「論語」、「孟子」),應分入「集部」(個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為例,體裁上分正史、編年、別史、雜史、載記等,全無道理與必要,其他詔令應分入法律類,時令應分入天文類,目錄應分入總類;以第三部分「子部」為例,老莊申韓等家,其實與「論語」、「孟子」無別,都應分入「集部」,其他譜錄中草木蟲魚應分入植物類、動物類,類書應分入總類,小說應分入文學類;以第四部分「集部」為例,「經部」、「子部」分過來的書,多可分入哲學類、法律類、文學類。……總之,四部分類,大體上說,「經」「子」「集」多是一類,「史」是另一類,四部分類實在只是兩部分類。分類、分類,分了半天類,最後只分了兩類,所謂分類,分了等於沒分,這叫什麼分類!以「孟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十七冊)*為例,孟軻自命是孔丘的傳人——「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他說:「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這是十足以聖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結論是:「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這又是十足以道統自承了。雖然這樣,在身分關係上,孟軻卻只不過是孔丘孫子子思的學生中的學生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韓愈推崇孟軻是直承道統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廟;到了元朝,他被封為亞聖;到了明朝,因為明太祖不喜歡他,吃了一點蹩;後來就一直風光,直到今天了。「孟子」一書共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個字,在內容上,理直氣壯固多,理不直氣壯也不少。中國人推理不合邏輯,受孟軻的影響應該不少。這部有影響的書,在圖書分類中,在北宋以前只是子書,宋仁宗後,才升段為經書,真是愈來愈走運了。走運雖然走運,但卻成了中國圖書分類胡來的一個樣板,中國人在思考上一塌糊塗,由此暴露無遺。
源遠流長的大功德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維口述的「給女作家陳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說:「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長子揚和寄來帶有燈光的放大鏡,強能看書。我發現讀了幾十年的書,卻往往有許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輕時看書看不懂,我認為腦筋有毛病。現在看書看不懂,我認為書有毛病。陳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歐洲回國,往見他父親(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對他說:『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興你懂得很多種文字,有很多書可看。我只能看中國書,但可惜都看完了,現已無書可看了。』寅恪告別出來,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國書籍浩如煙海,那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歲左右,我又見到他。他說:『現在我老了,也與夏先生同感。中國書雖多,不過基本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我很懊悔當時沒有問他到底是那幾十種書。」對俞大維這些話,你有何看法? □我覺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見地的,難怪陳寅恪後來和他同感。他們兩位,都是博極古書的人,最後竟有這種高明的覺悟,是很可注意的。蘇雪林「文壇話舊」中記聞一多,也有類似的情況。蘇雪林說:「別人鑽故紙堆,愈鑽愈著迷,終於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張中國文化是世界第一。聞一多早年時代何嘗沒有這種冬烘臭味?可是,現在的他卻是奇怪,竟與從前的自己走著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聯大一部分學生舉行了一個歷史晚會,張奚若、吳晤、雷海宗均有演說。聞氏曾說:『剛才張先生說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懷。中國這些舊東西我鑽了十幾年了,一個一個字都弄透了,愈弄就愈覺得「要不得」,現在我要和你們「裡應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對友人說:人家見我終日讀書,『以為我是蠹魚,卻不知我是殺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還恨那故紙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夏曾佑、陳寅恪、聞一多的覺悟,都是真正深知「中華文化」後的覺悟。陳寅恪說:「中國書雖多,不過基本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俞大維「懊悔」當時沒問陳寅恪「到底是那幾十種書」。我想,我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問世,已代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由於我的精挑細選,我的確已「把中國的東西整理出一個定品」,我化朽腐為神奇,終於給中國人提供了一點披沙揀金的好處,「集」舊中國「天下之書為一書」,這真是源遠流長的大功德了!(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