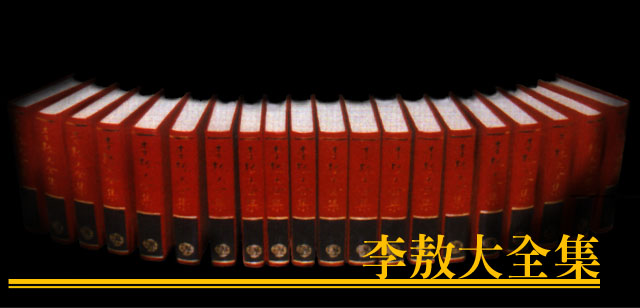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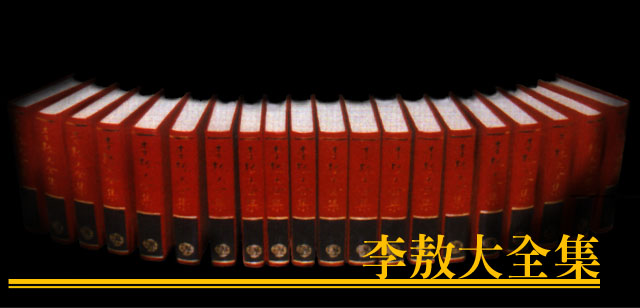
古書新見
清朝的張文襄公(之洞)在他的名著「書目答問」後面,曾有一段「勸刻書說」,其中要求「凡有力好事之人,若自揣德業學問不足過人,而欲求不朽者,莫如刊布古書一法」。他進一步指出:「但刻書必須不惜重費,延聘通人,甄擇秘籍,詳校精雕,其書終古不廢,則刻書之人終古不泯。……豈不勝於自著書自刻集者乎?且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
張之洞這段話,很能道出前人編刻叢書的心理,這種心理不外是「欲求不朽」、「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這種心理,九十多年下來,除了說法、名詞有所更動外,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但究竟由於時代的演進,使今人對於叢書,又多了三點意義:
一、戰亂的連續,使文物蕩然,所以搜集典籍,盡量予以流傳的要求,更加迫切;
二、新知的進步,使治學方法與取材標準,與前人不同,所以輯刊叢書的觀點,也不得不與前人有其同異,而不得不選取「新瓶裝舊酒」的方式;
三、印刷術的進步,尤其是影印技術的進步,使刊布圖書的方法根本改變,同時也改變了「珍本」、「秘本」、「孤本」等骨董觀念,使古代典籍不復成為某一階層人的獨得之秘。
由於增加的這些新的意義,使今人從事這一任務,自不能沿襲前人的手法,換句話說,再沿襲前人的手法編刊古書,就難免有落伍之譏了!
所謂前人的手法,最突出的一例,就是講究版本之說。對古書,非不可講究版本,但為一二校勘之便或幾個異文訛漏,就把一部書的功能和流傳性絞殺,則顯然是舊式藏書樓主的行為;同樣的,為了講究版本之說,整天光刊些無甚價值的僻書,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競賽」的常見經史之類,也不能不說是舊式版本學家的流毒,對鑑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業,為功究屬狹窄。
當年黃堯圃的學生,曾有過書無庸講本子的議論;俞樾的學生(章太炎)也提過讀書何必講究版本的疑問。這些見解,都是從「取其大者」的角度,來從古書選材的,他們並不斤斤於「輿薪之不見」的癖好,當然也反對先以偏為務,再以偏概全的專家孔見。
新時代整理古代典籍的標準,不應該以骨董式的版本為尚,也不該以鑑賞、校勘的用度為足,而該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務印書館的宋本「資治通鑑」,就沒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鑑賞和校勘上,雖然有它的價值,可是在普及和實用上,就遠不如它的重排本「資治通鑑」;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的無疏單注的五經,在普及和實用上,也遠不及藝文印書館的阮刻「十三經注疏」;同樣的,「仁壽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監本「史記」,在普及和實用上,也遠不如黃善夫本或殿本或瀧川會注本,這些例子,都說明了版本的考究,並不就是弘揚了文化。
除了避免以版本問題影響普及和實用外,書籍的選擇也是一個重要的項目。過去中國的圖書,都是在「七略」和「四部」裡打轉,本身是粗疏的、混亂的、偏頗的,並且是矛盾的。例如所謂「經」、「史」、「子」、「集」四部,儒家的書何以獨尊為「經」?而不同併為「子」,更進一步說,「子」又與「集」何殊?豈不都是個人才華的表現?並且,古人尊經等觀念,又無形中壟斷了其他學術的均衡發展,演變至今,在現代新知的光照下,許多書,古人所貴者,如今看來已是斷爛朝報;又許多書,古人所賤者,如今看來卻價值無窮。如今我們回首古籍,並不是止於把它們進一步分類(如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或杜定友「杜氏圖書分類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陣就算完事,而該大力發掘並認定真正值得現代學術「獺祭」的典籍,否則的話,只是引今泥古而已,離玩物喪志,也就不很遠了,「學術」云乎哉!
古書的重印,除了版本和選書以外,由於現代印刷術的進步,在規格上,又不得不注意配合時代要求,線裝薄面也好、綢函絲訂也罷,早已都是落伍的玩藝,都不應該再予以考慮。在國際標準的圖書館中,甚至平裝書都在不受庋藏之列,我們怎麼能再抱殘守缺,開時代倒車?所以無須採用舊式裝訂的方式,自無疑義。
中國近代的戰亂不斷,圖書上的損失早已無法估計,不論無意的被焚於兵禍,或是有意的聚毀於七塔,對文化而言,自屬有害無益。今天我們得現代印刷術之便,又趕上今日世界以研究「漢學」為顯學,乘機多刊印一些普及而實用的典籍,該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中華古籍叢刊」的問世,在取捨定奪方面,大致與上述主旨相近。有現代眼光的知識分子,必然會對這部叢書的選刊,有所肯定。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四月三十日
〔附記〕這是我十一年前,為「中華古籍叢刊」寫的序,原題「『中華古籍叢刊』緣起」,現在改名。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