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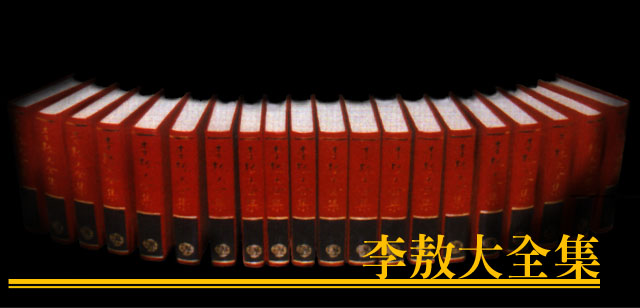
( 代序 ) 略
引子——巫醫與西潮
中國的醫學史,並不是什麼真的「醫學」史,而是一筆道道地地的「巫醫」史。 換句話說,不太客氣的說,中國歷史上,根本沒有真正的「醫學」。 中國傳統上關於「醫」的記載,最早的是神農、黃帝等的假歷史,後來年代較近,產生了所謂「醫」的始祖「彭」與「咸」,就是屈原所謂的「吳將從彭咸之所居」的「彭」與「咸」。 所謂彭咸,根本統統是「巫醫」。我們查查古書,很容易就看到: 「世本」:「巫彭作醫。」(「山海經」海內經注引) 「呂覽」:「巫彭作醫。」(「勿窮」) 「說文」:「占者巫彭初作醫。」 「世本」:「巫咸初作醫。」 (「玉海」六三引) 「世本」:「巫咸堯臣,以鴻術為帝堯之醫。」 「大荒西經」:「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 降,百藥爰在。」 「海內西經」:「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 可見「巫」和「醫」兩者,根本就是不分家的。換句話說,中國古代的所謂「醫」,根本就是神醫、就是「巫」、就是「迷信」的另一個名字! 「巫彭」與「巫咸」是殷商時代的人物。從這兩個所謂鼻祖以下,中國歷代都有所謂新一代——進化的、改良的一代——人物出現,都據說是愈來愈不「巫」了,愈來愈「醫」了,其實都是扯淡!他們不論怎麼改來改去,不論是什麼「華陀再世」「歧伯復生」都統統屬於萬世一系的巫醫系統。這個系統,直延伸到中華民國五十四年的所謂「中醫學院」,還沒有斷子絕孫,還是整年有數不盡的小「華陀」小「歧伯」出現,出現在這個可憐的國家,禍害這個可憐的民族,使他們吃樹根草藥、吞蟲屎黑湯。 但是,這個世界究竟不完全是「中華帝國」的世界,這個世界上畢竟還有進步的國家,有不吃樹根草藥、不吞蟲屎黑湯的民族,他們的進步與擴張,終於慢慢擠進了巫醫成群的東方古國,並且使十七世紀的中國康熙皇帝,首先嚥下了治療瘧疾的苦藥丸。 中國的「御醫」們治不好皇帝的瘧疾病,這只是一個在西方醫生面前失敗的開始;而西方醫生們此後的努力,也因這個事件而形成一個轉淚。從此以後,西化醫學的開始進口,也就愈來愈順利了。 西元一八○五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外科醫生皮爾遜( Alexander Pearson),進口了種牛痘的法子,使中國人開始少了一些麻哥;十五年後(一八二○),這個公司的又一個外科醫生李溫斯敦(LivingStone),與第一個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進口了一家施藥局,為中國人治療了一些病痛;再過了七年(一八二七),還是這個公司的醫生郭雷樞(T.R.Colledge)比較大規模的進口了醫療的工作,為中國人拓開了不少醫學上的眼光。 這個郭雷樞醫生,是最能了解治病有助於傳教的人,所以他乾脆發表了一篇論文——「對用醫生來在中國傳教的提議」(Suggestions with Regard to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這個提議,很受西方人的重視。到了一八三四年,終於第一個傳教醫生(missionary doctor)和中國人見面了,他,不是別人,就是中國第一個西方醫鈕、廣州「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的創辦人——伯駕(Peter Parker)醫生。在伯駕醫生創辦「博濟醫院」整整半個世紀後的第一年(一八八六),一個不到二十歲的中國青年人走近這個醫院,開始努力學做一個西化的醫生,他,不是別人,就是孫逸仙。 孫逸仙在這個醫院裏,曾經學會了一句開玩笑的禪話,叫做「有而不有,不有而有」。當他用這句禪話來向同學開玩笑的時候,他絕沒想到,他此後的生涯,竟是應了這八個字的偈語:——花了前後六年的日子去學醫,最後又把它拋棄,這不正正是「有而不有」嗎?本來認為中國的「膏肓之病」不能除去,而要「匿跡於醫術」,最後又重拾素願,「致力國民革命」,使「中華帝國」變成「中華民國」,這不正正是「不有而有」嗎? 「西醫與革命」,它不該只是一本歷史,而該兼有一種思想指南的身分。它告訴人們一個「有而不有」的具體例子,又給人們一個「不有而有」的明顯希望。讀了這本書的人,應該把它當作一支指針,在西化的浩蕩潮流裡,隨時校正它的導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