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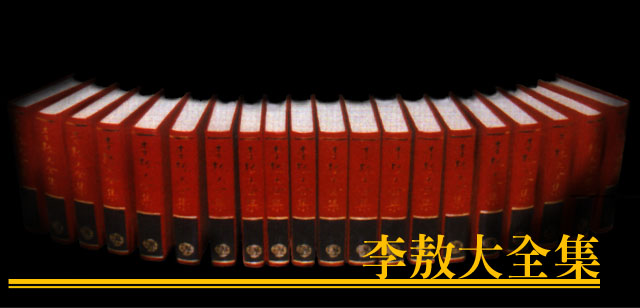
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的三月一日,我在「自由中國」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六千多字的文章——「從讀『胡適文存』說起」(現收入「胡適研究」,改題「關於『胡適文存』」)。文章發表後一年一個月,胡適從美國回來,約我到錢思亮的家裏,跟我說:「呵,李先生,連我自己都忘記了、丟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 那時我已有給他寫本傳記的意思,但是我一直沒跟他提起。我只提到幾部批評他的書,像李季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葉青(任卓宣)的「胡適批判」譚天的「胡適與郭沫若」等。對譚天的「胡適與郭沫若」,他根本不知道有這本書;對葉青的「胡適批判」,他回憶說:「二十多年前葉青寫完了這部書,寄了一套給我,要我答覆,我本來寫好了一封信答他,後來一想:葉青在書裏說我不必蓋棺,論就定了,在他眼中,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還能說些什麼呢?所以我一直沒有理他。」 如今,七年過去了,胡適之從生龍活虎轉入墓草久宿,從聲容笑貌變成一棺孤骨。但是,每當我在南港的高壓電線底下,走上了胡適的墳頭,我都彷彿聽到一種熟悉的聲音在向我感嘆:——「我已是死掉的人了,死人還能說些什麼呢?」 於是,我又撿起七八年前的心願,想給胡適寫部傳。不過這回不再是一本了,我決定給他寫一部十本的大傳記,我要用這一百二三十萬字的大傳記,讓「死掉的人」重新「活過來」,讓他重新「說些什麼」(註一),也讓我們「說些什麼」。 我所以發憤由我來寫這部傳記,另外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看到別人遲遲不肯動手,或做得實在令人不滿意。在胡適生前,我讀過胡不歸的「胡適之先生傳」;在胡適死後,我看過毛子水的「胡適傳」。這些簡陋的傳記都出於胡適的學生之手,基本的姿態都是維護他的,或是只有頌揚沒有批評的,同時在史料處理方面又過於粗疏,難免有很多錯誤。 十多年來,我遍讀有關胡適的一切著作,深覺不過是兩類而已:一類是近於酷評的( diatribe);一類是過度頌揚的(eulogy)。兩類共有的毛病,是不能用嚴格的方法訓練去接觸史料、解釋史料。於是,旌旗開處,胡適一出場,喊打與叫好之聲此起彼落,胡適一方面被罵得天誅地滅,一方面又被捧得縮地戡天。結果呢,雙方的感情因素是滿足了,可惜被搬弄的卻不是真正的胡適之!英國的大政治家克倫威爾曾罵給他畫像的人說:「畫我須是我。」( Paint me as I am)這句話,可以給任何想給別人「畫像」的人做為警戒。胡適之不是輕易被了解的人,所以他也不容易被論斷,沒有受過嚴格的方法訓練和史學訓練的人,沒有學會呼吸新時代空氣的人,是沒有辦法給他「畫像」的。做為一個對方法訓練和史學訓練稍有所知的人、做為一個對新時代空氣稍曾呼吸的人,我現在自告奮勇地來做這件大工作。我的目的不僅是「畫」胡適之的「像」,並且還要畫這個時代的像,我要畫出這個時代裏的大舞台、畫出它的喜劇和悲劇、畫出劇裏的主角和配角、畫出它的場地的布景、畫出布景後面的眾生相,也畫出戲台前面的千萬隻眼睛。 所以,可以這麼說,這部「胡適評傳」,不該單是胡適之個人的評傳,它是時代的評傳,它是以胡適為主角之一的時代的評傳。 所以,很可能的,許多人看了這部評傳會感到驚訝駭異,從正文來看,它可能是文學的;從腳註來看,它可能是歷史的(註二);從夾縫來看,它可能是無孔不入驚世駭俗的。它的結局是:君子既不喜歡它,小人也不喜歡它,只有跟李敖一個調調兒的,才會喜歡它。 但這都沒關係,這都不影響這部評傳的方向和進度,一個載浮載沈的傳主,被一個亂蹦亂跳的作者來寫他、晝他、捧他、搥他,這該是中國傳記文學史上的新嘗試。——只有在新時代裏才能肯定這種嘗試,只有這種嘗試才能延伸另外一個新時代。 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四)二月二十四日胡適死後二周年的深夜
註一:我熱烈希望凡是和胡適有關係的人,都能幫助我這個使他「說些什麼」的計畫。這意思就是說,凡是知 道或保存有關胡適的言行、文件、信札、圖片、稿本等材料的人,都歡迎能夠提供、惠借,好使這部評 傳增色。在傳記文學不發達的中國,在這個動亂的時代,試問能有幾部一百二三十萬的傳記來收入你所 知道或保存的材料?所以請你不要錯過這個廣布流傳的機會。註二:我盡量不在正文裏摻入繁瑣的歷史考訂,我的目標是「正文輕快,腳註詳細」。這種做法是一種費力不 討好的工作。我所以不能放手寫文學式的正文,而要兼顧歷史性的腳註,乃是因為有關胡適的基層史料 工作還沒有人做好,所以我不能自自在在的走史特拉齊(Lytton Strachey)、莫洛亞(Andre Maurois )等人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