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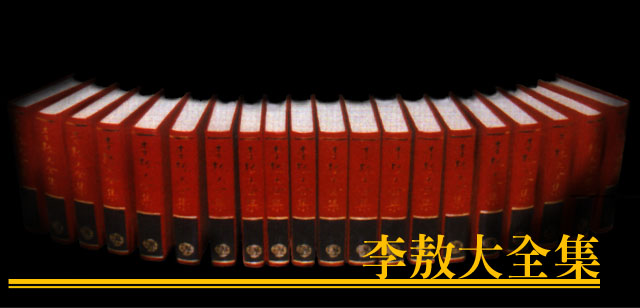
胡適先生死在五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三點鐘,我寫下了這幾段文字:
兩年十個月來,我一直沒見到他,當然再也不會見到他,——一個最能播種的人兒,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種子了! 這幾段文字寫好後,我並不打算發表,所以我改寫了一篇「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發表在三月一日的「文星」雜誌裡。 ﹡ ﹡ ﹡ 胡適先生走進「地獄」後,眼看就快兩年了。兩年來,真可說是一個既「冷漠」又「吵鬧」的局面。 何以說「冷漠」呢?這是專指胡適生前圍繞在他周圍的人說的。他們這批人,在胡適生前儼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門生、乾女婿,是「蟠龍大花瓶」的贈送者,是生日酒會的拜壽者,是「胡適合會」的「標會」者,……可是在胡適倒下以後,幾乎在「屍骨未寒」的當兒,他們就變成了「不認得耶穌」的「彼得」。「新約」路加第二十二章裡,有這樣的故事:
這真是一個含義深長的故事!這個故事在耶穌死後一千九百年,居然在臺灣來了一齣全新拷貝——胡適的親愛的「彼得」們,紛紛露出了他們的嘴臉,他們和當年彼得不同的一點是:彼得還會羞慚痛哭,還會在日後做個傳布耶穌思想的使徒,可是他們呢?他們都不會,他們只會在胡適的生日忌日裡來一番「告朔餼羊」,對遺照三鞠躬以後,一哄而散,坐車回家。 記得胡適死後不久,胡虛一先生在「民主潮」第十二卷六期(五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裡,翻譯了一篇「民主政治的兩種觀念」,他在譯後記裡有這樣一段話:
胡虛一先生這段感嘆,還只不過是專指胡適臨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現在胡適死了快兩年了,在這兩年裡頭,胡適的「門生高足」更是安靜得可愛了,他們安靜地看著,看著那個「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來開創一個「吵鬧」的局面。 * * * 所謂「吵鬧」,應該從頭說起。 民國五十年的年底,我應「文星」雜誌編者的邀請,為他們寫了一篇「播種者胡適」。這篇文章帶來了大是非和大麻煩,進而釀成了一次大筆仗,後來這次筆仗分成了兩個圈圈,一個圈圈是「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論戰」;一個圈圈是「關於播種者胡適的論戰」,前者的主要對手是徐道鄰先生和胡秋原先生;後者的主要對手是葉青(任卓宣)先生和鄭學稼先生,大家打做一團,十分熱鬧。 在「播種者胡適」發表以後,贊同或變相支持我這篇文章的人很多,例如香港「自由報」的社長雷嘯岑先生(馬五先生),「中國學生周報」中的若蘭先生,「展望」雜誌中的孟戈先生,臺灣「作品」雜誌中的蘇雪林先生,「民主中國」雜誌中的牟力非先生,「文星」雜誌中的王洪鈞先生、東方望先生、田尚明先生,……都是形諸文字的例子。此外在口頭上面、書信方面,我也得到了不少的支持和同調。 當然相對的,反對我的浪潮也就澎湃而來,它們的大本營就是我所謂的「三大『評論』」:「政治評論」「民主評論」和「世界評論」。在這些刊物上,我陸續遭到許許多多的攻擊和謾罵,可是我實在懶得理他們。對「播種者胡適」的問題,我只寫過一篇「為『播種者胡適』翻舊帳」的文字,來答覆葉青先生和鄭學稼先生,其他不入流的人和那些不入流的文字,我一概不理。即使葉、鄭兩先生,我也只答覆一次,當他們第二次向我使出回馬槍的時候,我也懶得辯駁了。 我為什麼不再答覆葉青先生和鄭學稼先生?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我覺得對這兩位先生,從文字上枝節上跟他們辯論是沒有用的,也是不能了解他們的。要了解他們必須從他們的「基本思路」(primordial motives and images)上一刀扎下,從「基本思路」上來探討他們寫文章時的理論背景和「心理運作」(mental operation)的過程。當我對兩位先生過去的歷史有所了解之後,當我恍然大悟他們的「前期快感」(fore-pleasure)是什麼主義以後,我不禁阻止我自己說:「算了罷!放他們去罷!」 * * * 談完了「冷漠」和「吵鬧」兩個局面以後,我覺得我該談談「播種者胡適」本人。我先抄「世界評論」第十年第五期(五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中,周伯達先生的「現階段中西文化論戰之平議」裡的一段話:
這段令人發笑的「推斷」,簡直荒謬得不值一駁。其中有一點,所謂胡適「深為」「賞識」我這篇「播種者胡適」的問題,我覺得大可不必請「今後注意考據的人」來「考出這個秘密」了,請讀讀楊樹人先生的文章就得了。楊樹人先生在今年二月一日的「文星」七十六期上,發表了一篇「回憶一顆大星的隕落——記胡適之先生最後的三年」,裡面有一段寫胡適先生對「播種者胡適」的不高興:
這大概就是周伯達先生所說的胡適先生對「李敖這位年輕人」的「深為」「賞識」罷? 據錢思亮先生告訴我,胡適先生死後,他整理遺稿,發現了一封胡先生讀了「播種者胡適」後寫給我的信,可惜這封信因為被胡先生的近親好友「妥為保管(封鎖?)」了,所以直到今天,我這個收信人還不能看到。 我知道我這篇「播種者胡適」會三面不討好:罵胡的人會說我捧胡,捧胡的人會說我罵胡,胡適本人也會對我不開心,這都是無可奈何的事。 好在我是搞歷史的人,搞歷史的人只曉得追求歷史的真相,不計其他。胡適先生是我們這個時代裡的一名朝山香客,他的所作所為、他的真面目,都對我們這個時代有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值得一個搞歷史的人去結一結帳。基於這個理由,我除了寫一部「胡適評傳」外,決定再印行這本「胡適研究」。 * * * 這本「胡適研究」,共收了我自己七篇文字:第一篇就是「播種者胡適」,這是一篇重要的文字,一篇「禍首」。第二篇是「為『播種者胡適』翻舊帳」,也是一篇惹是非的文章,可惜這篇文章寫完那天,正是胡適「遽歸道山」的日子,胡適生不及見,反倒成了他的安魂曲。這兩篇文章都有許多和它們有關的文字,可是限於篇幅,我只能挑出八篇,做為附錄。 第三篇「三人連環傳」,是寫梁啟超、胡適、徐志摩三個人的。這種連環寫法,也許可給傳記文學開一個有趣的例子。 第四篇就是「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這篇不到一千字的文章,最為某些人所欣賞,他們覺得能用這樣少的字數、刻畫出這樣多而深刻的意思,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我對這篇文章也頗得意。不料居然引起讀者劉星先生的誤會,在報上痛罵我,我只好把這種批評,請到這篇文章的背後,做為附錄。 第五篇「胡適對蘇俄看法的四階段」,是寫胡適的一段思想變化的歷史,可算是「胡適評傳」中的一小節,這段歷史,我在「胡適評傳」中還要細細寫到它。 第六篇「關於『胡適文存』」,是一篇「特殊的」書評。最初登在「大學雜誌」,後來刪了一部分,改登「自由中國」。這本是我高中二年級時候所寫的一篇文字。胡適先生後來告訴我說:「雷震特別寫信給我,推薦你這篇文章。」 第七篇「評介『丁文江的傳記』」,也是一篇書評。對這本書缺點的指摘,我本已寫了一封信給胡適先生,可是他在出版時都沒有改正,我頗為失望,也頗覺得他在這一點上未免不夠虛心,他只是笑嘻嘻地跟我說他看過我的信了,如此而已。總之,對「丁文江的傳記」這本書,我覺得它是一本缺陷很多的傳記。 * * * 編完這本小書以後,我感到一種輕快。胡適先生跟我壓根兒沒有什麼「深厚的世交關係」,我也不是張鐵君發行的「學宗」(三卷二期)中所稱的「被胡適全心全力支持的西化太保」,但胡適跟我之間,有許多緣分卻是事實。這些事實將來我總會把它們寫出來,不過那也許要在「天下太平」之後。現在我只把這本「胡適研究」先印出來,用來懷念這個去世已經七百多天的老人,一位時常要對我皺眉頭的「老朋友」。 五十三(一九六四)年二月六日在臺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