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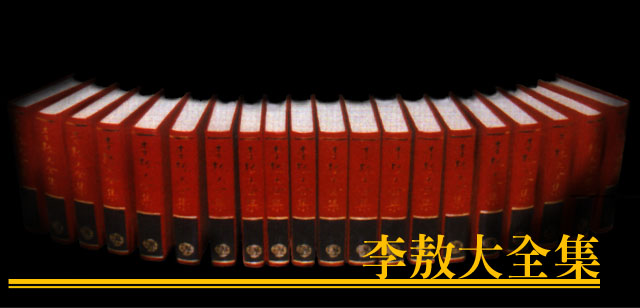
李敖文章如滾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黑髮文豪書桌上, 慣看秋月春風。 一瓶啤酒醉相逢, 上下古今事, 都付笑談中。 ——改寫「三國演義」題詞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的七月裡,在臺灣島上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從七月二號開始的「秀嫚信箱」,由劉秀嫚執筆,發表在「中華日報」;一件是七月五號開始的「上下古今談」,由李敖執筆,發表在「臺灣日報」。我所以說這是中華民國的兩件大事,就因為這兩個專欄的主持者都是名人:一位是名女人,是美國選美場合中的東方美女;一位是名男人,是英國「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中稱道的「一個得人心的英雄」(a popular hero)。如今這一女一男,不約而同,在哥德所謂的「戀愛季節」(五月)之後兩個月,分別在報上宣傳人生的大道理,這不是中華民國的兩件大事,又是什麼呢? 提到劉秀嫚,我曾寫文章戲呼她是「最使我著迷的美人兒」,不料這話引起了大謠言,——這個社會不允許男人純粹有「著迷的自由」。謠言說到劉秀嫚和我正在「鬧戀愛」,臺灣北部的報紙和東部的報紙,都有文章來捕風捉影,非常好玩。去年十月三號,「中華日報」上有洪敬思先生的一篇「從絢麗歸平淡——劉秀嫚棄虛榮」的報導,就「傳說她跟李敖在鬧戀愛」一點上,有段話說:
對這一點記者先生派給我的好福氣,我只能說,到現在還不是真的。 今年二月二十五號,我從臺中打官司回來,在車上又看到「中華日報」(又是「中華日報」!)記者劉一成先生的專欄——「婚謠困擾劉秀嫚」。裡頭說:
照劉秀嫚這種說法,我李敖真覺得我自己「罪孽深重,不自殞滅」,亂寫文章搬弄,以致禍延我們的美人兒,實在該罵,——該被劉秀嫚的前校長居浩然先生罵。挨罵以後,我會大徹大悟,此生絕不再把「最使我著迷的美人兒」的名字透露,咱要把她的名字「長捐心底」,永遠偷偷摸摸的,那才好。 劉秀嫚在「中華日報」的專欄,似乎發展得並不順利。斷斷續續,最近好像又停擺了,這是很可惜的事。我所以說它可惜,理由很多,我必須加以進一步的解釋。 所謂「秀嫚信箱」,它的真正意義不單在「信箱」的執筆人寫些什麼,同樣重要或更重要的,是「信箱」執筆人以她的身分和地位向人們宣示些什麼。換句話說:「秀嫚信箱」的意義,不止於普通的一個「信箱」主持人的意見表達。它的意義,是告訴人們「劉秀嫚的意見」,告訴人們以我劉秀嫚的身分和地位,要說些什麼。 這種分際,就是一個「普通人說」或「什麼什麼『夫人』說」,跟「劉秀嫚說」的分際。它們對群眾的影響力,是絕對不同的。換種說法,就是「劉秀嫚說」的影響力,要比一般阿貓阿狗的「方塊」或「信箱」來得大;劉秀嫚的「說服力」,要比一般文字的效果來得多。 劉秀嫚的重要就在這裡,而她的苦惱也就在這裡。 劉秀嫚為什麼苦惱呢?我沒有跟她個別談話的機會,也沒「訪問」過她,對她的苦惱,只有憑我對女人的老練來「猜」。這種「猜」出來的結論,可能距事實極遠,但總不失為一種「大膽的假設」,因此我仍願公布我這些「猜」出來的判斷。 我「猜」劉秀嫚的「信箱」發展得並不順利,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寫文章的訓練不夠、思考問題的訓練不夠,因此她執筆寫文章、答問題,只是普普通通的老生常談而已,並沒有太多的真知灼見。我們試看她的幾篇專欄,如七月二號的「孝道與學業」、七月四號的「不要生老師的氣」、七月十六號的「幫助孩子改過吧!」、七月十八號的「一分鐘與一生」、七月二十七號的「又快又充實」等等,只不過都是些平平的文字,甚至還有一些不自覺受傳統影響而發生的錯誤觀念。這些表現,時時追求進步的劉秀嫚自己,也許會感覺出來,於是 她對自己的意見也未免不滿意,或者眼高手低力不從心,因而她的文章,未免距她的美麗過遠,跟她的風華絕代太不相稱,再這樣寫下去,實在難逃「用非其長」之譏。在這些情況底下,「秀嫚信箱」發展得不能順利,應該是很自然的事。 我做這些「猜」想,並沒有責備劉秀嫚程度不夠的意思。恰恰相反,我非常肯定她的程度。劉秀嫚比起今天一般大專學生來,她的程度——各方面的程度——實在很不錯。「很不錯」三個字,出自刻薄寡恩的李敖之口,任何人都可知道這已是很捧場的話了。以劉秀嫚的努力、上進、謙沖、重感情、不改本色、不忘貧苦大眾,……她可說是年輕一代的「小聖人」。對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小偶像,我們似乎沒有再多所責備的理由。 但是,對劉秀嫚今天所處的地位來說,我老是覺得她可以多做點什麼,更積極的做點什麼。她對群眾的意義,不該只是一個「孝順的孩子」、一個「努力的大學生」、一個「技巧熟練的廣播節目主持人」,或是一個「小周璇式的女歌手」。她個人的行動,除了表演、訪問、勞軍、剪綵、廣播劇、散發簽名照片等等以外,似乎應該更進一步,為廣大的中國群眾做點更積極而有意義的好事。只有這樣發展,才更能配得起她的善良和美麗、才更能襯得住她那塊「中國小姐」「環球小姐」的招牌、才不辜負她的「小偶像」的地位、才對得住我們青年朋友對她的殷切期望。只有這樣發展,劉秀嫚才能在平凡中孕育偉大、孕育永恆的偉大。 在中國傳統的觀念中,一個女人的路線,只是「賢妻良母」的路線。這是一條單行道,一條非常狹窄的單行道。夾在這條單行道兩邊的,是丈夫的拖鞋、子女的尿布、廚房的鍋碗瓢盆、鄰居的八舌七嘴。故中國的女性,只是男人的附屬品,她的一切生老病死、富貧榮枯,都以丈夫的變化為函數。她自己,並沒有真正的自己。中國的傳統觀念,也從不允許女人有她的自己。傳統的女人,在「賢妻良母」以外,多認識一些字,多寫一首小詞小令,已屬難得,並且也接近「大逆不道」的邊緣,因為「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的「完成」,並不以「才」為充要條件,甚至「才」還是她「不守婦道」的張本。所以流風所及,中國歷史上至多只有偉大的「母性」,並沒有偉大的「女性」。中國歷史上不會有「女思想家」、「女社會改革家」、「女叛徒」、「女飛行家」……中國的傳統不鼓勵女人去走這些路,要走也走不成。中國的女人不論長得多麼高,也要被男人踩在肩膀上。正所謂女高一尺,男也高一尺,因為女人那一尺,就是間接為男人高的。 但是物極必反,天道好還。近百年來歐風美雨的吹打,女人的地位竟告普遍抬頭。在整個世界的女人「蠢動」趨勢裡,中國的娘兒們自然也不例外。中國的陰性們逐漸知道她們的力量是非同小可的,她們逐漸知道她們美麗的力量、陰柔的力量、教化的力量、表演的力量,以及和平改革的力量了。她們逐漸知道許多男人費力辦不到的事,她們居然可以輕易的辦到了。試看「十四萬人」的男子漢,不能使英國僑民看到青天白日旗;可是一個李秀英,卻可使英國鬼子把中國國旗升上去。這種「佳人的力量」,豈不活生生的教我們男人臉紅嗎?這種偉大的成績,豈不是鐵的事實嗎? 舊時代的女性們,她們對人群的力量,很少是正面的力量。她們只是側面的「禍水」的力量。一個海倫(Helen),可以使人民連年爭戰;一個克李敖芭特拉(Cleopatra),可以使群雄每日相砍。這些舊時代的「女英雄」(heroine)們,和她們影響下的「英雄」(hero)們,在遙遠過去的所作所為,早已使我們不敢領教。他們的「豐功偉業」,大都建築在人們的血淚之上,他們總是在「澤國江山入戰圖」的狀態下,完成「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局面,在「血流漂杵」的慘象裡,奴役這個,又打倒那個。 但是,從卡萊爾(Thomas Carlyle)出現以後,他的「英雄與英雄崇拜」言論,為一般的「英雄」定義,做了不少的修正。在卡萊爾眼中,不但神明、帝王等可以成為「英雄」,就是先知、教士、詩人、文人也不失為是「英雄」。到了今天的二十世紀,「英雄」的定義已需要更新的修正。一般什麼神明、帝王,早該踢出「英雄」的行列,而該代以美人、戲子、電影明星、TV的設計者、沙克疫苗的發明者、太空人、潛水人、試飛人。……他們這些,才是新時代的「英雄」,他們比舊時代的所謂「英雄」要高明一萬倍、偉大一萬倍。舊時代的所謂「英雄」們,他們要整天砍別人腦袋、切別人指頭,才能成為「英雄」,然後發動大量的文警,製造宣傳,使人們對他們「愛戴」「崇拜」,誤以為他們是「英雄」。但是新時代的「英雄」們,他們卻不這樣,他們直指人們的內心深處,使人們從心底發出對他們的愛戴崇拜,不再砍殺流血,也不需要斷頭臺。他們只憑他們的智慧、好心、靈巧和美麗,再加上對人無害的成名欲望,交織成一個百花齊放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是和平式的發展抱負,運動會式的公平競爭,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為的操守,為目的而又考究手段的道德。新時代的「英雄」們,使人們皈依自己的方法不靠武力、不靠特務、不靠強迫,也不靠鞭子。他們所靠的,完全是本身的可愛、本身的吸引人、本身的和平溫煦的手法。新時代「英雄」的造形,絕不像舊時代的橫眉怒目、鬍子亂撇;他們極像司馬遷筆下的「英雄」張良,面如「婦人好女」,並且可能就是「婦人好女」。在這些「婦人好女」中,我對劉秀嫚寄以很大的希望,我要投她一票。 劉秀嫚成為「英雄」「英雌」的基本路數,必須建築在她的一些基本改變之上。她必須徹底認清世俗的表演、剪綵那一套,絕對不是有意義的行徑;做「孝子」、「好學生」那一套,也不是終極的目標。她該想想陸放翁那「欲求靈藥換凡骨,先挽天河洗俗情」的詩句,然後進一步了解:「洗盡鉛華」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洗盡」她在這個地區多年被感染、被輻射的「俗情」。她該知道:她的見解與頭腦,可能遠不及她的美麗的程度,不但不及,甚至非常不成比例。 她如果不努力拉近這個比例,她必將成為一個世俗的美人,終將凋謝而去,變成每一個「中國小姐」「環球小姐」的下場,並無例外。 劉秀嫚今日的路線,只有一條,就是下決心不再陪世俗來串假場面、下決心走她自己的覺醒生活。即使做個「女叛徒」,也在所情願。有這種決心以後,她該知道她目前的生活方式,大有問題;她給一般青年男女們的「言教」與「身教」,也大有問題。她在洗盡「俗情」以後,該開始尋求「靈藥」,來洗心革面、來脫胎換骨。而這種「靈藥」,不是別的,就是「新思想」與「新知識」。 有過「新思想」與「新知識」訓練後的劉秀嫚,再出面主持任何節目、任何信箱,必然都得心應手,顛倒眾生。那時候的群眾思想,將都貫注在她的焦點之上,以她的思想動向為轉移,美人步亦步、美人趨亦趨,對國家的貢獻、民智的洞開,將有意想不到的奇效。 我上面這種議論,實際上有我的推理根據。凡是稍懂群眾心理的人,都可知道「喚起民眾」的方法,絕不是硬朝他們餵「黨八股」跟「清一色思想的藥丸」。我們必須引起他們的興味,然後施以正規教育和機會教育。我們必須深通「大眾傳播」——居浩然先生譯為「大眾交道」——的一切原理和技術,借助於一切有效的工具(如文字、書籍、傳單、壁報、雜誌、報紙、演說、廣播、電視、電影、幻燈、畫展、博覽會、交通設備等),普遍的、深入淺出的,展開思想上的明示或暗示工作,用來變化群眾的思路與氣質,一齊走向現代化的道路。在這種「喚起民眾」的大目標下,我們必須放棄學院派的枯燥論文,放棄書獃子的愚笨面孔,放棄一本正經的不通文字,轉而走向「挑逗大眾」的路線、吸引大眾的路線。使他們放棄孔夫子孟夫子程夫子朱夫子,放棄釋迦基督黃三太二郎神,放棄牛克斯馬克斯豬克斯羊克斯,轉而對我們著迷,為我們沈醉。這樣子的「挑逗」和「吸引」,有時候,學院裡或深山裡的思想家們,必須向「中國小姐」或「電影明星」一類的人物學習學樣。看他們是那樣的受歡迎,然後會覺得自己不被歡迎乃是一種恥辱——這只證明了學者同思想家們跟群眾脫節,並不值得孤高自傲。 在目前的世界趨勢裡,真正能「喚起民眾」的人,大部分都是學者和思想家以外的人物,這些人物出面來鼓吹學者和思想家的意見,所收的效果,要在比例上大得多。馬龍白蘭度出面主張廢止死刑、查爾赫斯頓出面主張黑白平等、法蘭克辛納屈出面關切總統選舉,……這些舉動,都容易引起天下風從的效果,都比什麼專家什麼學者的呼籲來得靈。大事如此,小事又何獨不然?一個「黑人牙膏」,牙醫師的千言萬語鄭重推薦,遠趕不上「凌波小姐也愛用黑人牙膏」一句話;而「黑人牙膏」再加上「樂蒂小姐也愛用」,效果也就更周全,——至少看過「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影迷,此生再也不敢反對「黑人牙膏」了! 可憐的是,中國的現狀是學院裡的人物跟群眾脫節;而跟群眾不脫節的一群又俗里俗氣,完全不知道「思想」為何物,——他們只是盲目帶領群眾而已,恰像那瞎驢子推磨,只是在原地上打轉;萬一脫韁而出,也只是反動的開倒車。他們永遠不懂得什麼叫「廢止死刑」?什麼叫國計民生? 如果中國的學者和思想家以外的得人心的人物,能夠出面關切思想運動、政治動向、社會改革,那麼收效一定很大。尤其是一些有清望的人,如果他們能善用他們的清望,肯下海做好事,不輕易做人情面子的事,我們群體的進步一定來得更蓬勃、更快。就目前的環境說,有帶頭作用的老一輩和中年一輩的人物,實在已經少得可憐,而青年一輩又多在機會缺少的高壓底下,爬不起來。因此偶爾有脫穎而出——不管是從那一個路數脫穎而出——的青年一代,他們的責任,也就更來得重大,也就更不限於「獨善其身」就算完事。換句話說,他們不應該僅僅是一個「作家」、一個「中國小姐」、一個「電影明星」、一個「企業家」。他們應該不僅僅是做佛經中的「自了漢」,應該聯合起來,加做些別的、多說些別的。例如一個十八世紀人權保障的老題目,值得大家全體注視;一個非法判決的死刑案件,值得大家一致聲討。在一個共進的群體裡面,個人——尤其是有才智有地位的個人——不應該只限於「專業」上面的注意,他應該打破傳統的什麼明哲哲學,偏偏要走出來,多管些實際並不「閒」的「閒事」! 我的青年朋友何秀煌先生,最近在「文星叢刊」第一六八號,出了一冊「現代社會與現代人」。在書裡,他重印了一篇叫做「我們應該打破容忍與沈默」的好文章,他說:
秀煌這段提示,我完全同意,我甚至同意他在文中所列舉的一些看來「似是小事」的例子,因為秀煌的真精神並不是斤斤計較「小事」的人。秀煌的真精神是如他所說的:
讀了「秀煌」的文字,我們再來看看「秀嫚」的作為,我不得不指出:以劉秀嫚popular身分與地位,她做得實在不夠。這種不夠,嚴格的講,實在不該怪她,而該怪何秀煌、李敖之流。怪李敖他們沒有及早進行「提醒」和「遊說」的工作,以致劉秀嫚只能成為一個十六年來臺灣教育訓練出的標準樣品,而不是一個灑脫絕世滿不在乎的女人。她不會奇思遐想、不會特立獨行、不會攻擊、不會反叛、不會氣一氣老頭子。她只是那麼馴順可愛,並且以「言教」和「身教」,向青少年們說明,我們該如何「聽媽媽的話」! 當我眼睜睜的看到,我們脫穎而出的青年朋友們,並沒有使出真正「青年」的路數和解數的時候,我覺得我必須挺身出來,「打破容忍與沈默」,嚴格的指摘他們、批評他們、糾正他們的導向。我絕不在乎別人說我以老大自居,我是老大,並且很老很大,我絕不坐視「我本將心託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的現象蔓延,我要叫。 西方近代最才華蓋世的天才女子鄧肯(Isadora Duncan)有一次向蕭伯納開玩笑說:「以我的美,配上你的聰明,生一個小孩,那多好!」蕭伯納答她道:「萬一生出來的,竟是我的醜,配上你的愚笨,那該多糟糕!」我舉這個笑話,為的不是別的,而是引喻我的一個妙想。 我的妙想是:在我們目前的現狀下,我李敖雖然仍天才橫溢、鬥志不衰,可是畢竟因三年來樹敵太多,相對的增加不少敵意和阻力,也增加了不少對我有成見的傻瓜。所以同一句話,不出自別人之口而出自我李敖之口,外面的反應就多少有點不同。常常是一句真理,因為是我李敖說的,有些傻瓜們就難免賭氣:「李敖說該這樣,我們偏不這樣!」「李敖是什麼東西呀!他要我東,我偏要西!」可是,當這句真理,不由我李敖說出而改由劉秀嫚說出的時候,它的「說服力」就會比我強得多了。美人在這個世界上,跟五十分上下釐米的電線一樣,是阻力最少的物體。這種物體,在消極方面,可以減少不必要的猜忌;積極方面,又可以增加群眾的信心。基於這種認識,我開始凝結我的妙想是:——劉秀嫚若能寫出我李敖這樣的奇文,那多好!她的美麗若加上我的天才,那多好!我情願挖空我的腦袋,把我的天才全部送給她,叫他媽的上帝徹底做一個不公平的上帝:一方面使美人兼做才女;一方面使「文化太保」變成「文化白癡」。在李敖「交出棒子」以後,改由劉秀嫚做思想家、批評家、史學家、散文家、傳記家、演說家,以及戰士和情聖。……那時候,劉秀嫚將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鄧肯、我們的喬治桑、我們的克萊拉巴頓(Clara Barton)、我們的山額夫人、我們的BB和莎崗。她那多方面的前途,將因多方面的突破而變得無可限量,她對我們國家的貢獻,也將超過每一個賢妻良母月貌花瓶的女人。 我這些話,人們不要又以為是我酒醉後的瘋話,這些話不但不瘋,並且還是一個偉大而周密的構想。這個構想的基本論是我想朝群眾使用「美人計」,用美人的春風,施開明的秋雨,不再由我來表演「秋風秋雨愁煞人」的場面。這種苦心,我想必然得到我的敵人和睜著眼睛羅織我罪狀的人的贊同;它如果成功,敵人和我都可安心睡大覺,或者湊上一桌,盡棄前嫌,打他八圈麻將。 我在這篇文章中,天南地北,扯了八千字,還在扯劉秀嫚「秀嫚信箱」的題外話,未免太囉嗦了。並且這樣扯下去,好像是在給「秀嫚信箱」寫序,而不是給我自己的「上下古今談」寫序,這又未免太顛倒乾坤。所以我還是來談談我的「上下古今談」罷! 我應「臺灣日報」發行人夏曉華先生之命,寫「上下古今談」的時候,我們的朋友張繼高(吳心柳)先生對我說:「我包你寫不過兩個月!不到兩個月,你們就會受到壓力,而不得不停止。我願跟你打賭。」 對張繼高先生的「預言」,夏曉華先生不服氣,我也不服氣,我們不信。我們開玩笑說,至少要寫它六十一天,要比張繼高的「預言」多一天。於是「上下古今談」便嘩哩嘩啦,開始上下古今的談起來了。 這個專欄一出世,不出我們預料的,「外界的壓力」立刻在四面八方飛來了。當然啦,這些「壓力」是朝夏曉華先生頭上飛的,而不是在我腦袋上轉的。所以常常是在夏曉華先生費勁應付外界麻煩的時候,我正躺在家裡睡大覺,並且睡得十分自在。睡醒以後,我挖著腳指頭對我自己說:「管他媽的什麼麻煩呀!你已經很窩囊了,夏曉華比你還窩囊。發表這些窩窩囊囊的文章,若還構成罪狀,『他們』真未免太小氣了!看『他們』滿口仁義道德、自由民主,按說不像是小家子氣的人呀?怎麼一碰到我,『他們』就小氣起來了呢?」於是,我把臭腳丫子一踢,就起床寫下一篇了。我懶得再想,寫它一天算一天! 就這樣的,我的「上下古今談」從七月五號開始,一直寫到八月二十七號,一天沒斷,足足寫了五十四天。其中有「李敖不可怕」和「判案不是猜謎!」兩篇,因故未能登出,所以一共是五十六篇。我把這五十六篇文章,稍加訂正和復原,配上附錄文字,就成為這本「上下古今談」的小冊子。 我為什麼沒有在八月二十七號以後,繼續寫下去呢?這個問題我現在不便回答,只有等到我八十歲寫回憶錄時再公布,或者等我死後,由我的乾孫子來公布。總之,目前此時此地,本人恕不公布。有人要好奇,就好他的奇去罷! 「上下古今談」不談了以後,我正式寫信給夏曉華先生,推薦劉秀嫚來掌握這一方之地。套一句古話,這種作風,叫「薦賢自代」,也叫「退讓賢路」。雖然在事實上,我自己本不失為是「當代大賢」,只可惜我賢得惡名四溢,只可嘆我賢得罪狀昭彰。所以不得不因故學學歐陽修,「避此人出一頭地」。我希望夏曉華先生用不衰的禮遇,正式敦請劉秀嫚來主持這一個專欄;也希望劉秀嫚用長駐的青春,來走上這被李氏壓路機壓過的大路。我相信劉秀嫚這樣做,在我們青年朋友的警戒和督促下,必然是一個新面目的起點。我祝她好運! 我清楚的知道,在我那些數不清的「不良紀錄」中,由於我這一篇「代序」,必然增加一條新的「不良紀錄」。為了使撰寫紀錄的「未來牌友」少一點麻煩,我現在代為擬定草稿一則,以供參考。文曰:
這條代擬的草稿,我想必然可供有關人士的採行,不必另做了。還是謄出時間,多練練「雙龍抱」和「全帶七」,那天下戰書來比賽,我李敖絕對奉陪,來它三十二圈,打個你死我活,不亦快哉! 「文星」第九十五期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 |